馬祖辭典之六:丁香魚
- matsu food

- 2019年8月1日
- 讀畢需時 4 分鐘
已更新:2019年12月25日
作者:劉宏文
初來台灣,在市場賣乾貨的攤子前看到丁香魚,雖然賣相不佳,灰灰潮潮的堆在塑膠盤子裡,仍然指著塑膠盤問:「丁香魚怎麼賣?」老闆抬起下巴看看我,語帶輕蔑地糾正:「遮洗呼拉(吻仔)魚,黑洗丁香魚啦!」他所說的「丁香魚」體型較大,乾巴巴地每尾約2、3公分長,銀色的魚身裡還可看到黑色的內臟。這種小魚質地鬆垮,嚼起來略帶一絲苦味,怎麼夠得上「丁香」這麼美的名字?記得小時候,父親稱這些雜魚為「ㄨㄟˋ ㄧㄤ」,是一種很賤價的小魚,混在蝦皮群裡撈捕上岸,煮熟後與蝦皮一塊攤在竹屏上曝曬、風乾。我們家鄉捕蝦皮的漁家都很大氣,一般都讓婦女、孩童在成片的蝦皮中剔撿這些雜魚,帶回家加一些紅糟煨煮,盛在鋁製的菜盆子裡,佐地瓜飯倒是很對胃,就那麼一小盆「ㄨㄟˋ ㄧㄤ」,一鍋蕃薯就見底了。
撈捕丁香魚的季節都是在立春後、穀雨前。此時雨水充足,草木滋長,豐沛的水氣來不及升起成雲,就濃聚而成大霧,一陣一陣像「掉雨」一樣,鋪滿山巔海岸,長達兩三個月的霧季於焉開始。家鄉人不說「起霧」,而說「落霧」,霧不是虛無飄渺地起自海上,而是厚厚實實地從天而落,翻湧在島上所有的輪廓與細節中。霧中的人事與景物混沌不明,於是乎家鄉人說母語的聲量都粗獷高昂,語調也迅猛急切,一字一句穿透沈沈大霧,敲打著山巔海湄,在無數個異鄉遊子的夢中迴盪呼喚。
就是在這樣的霧天,空氣潮濕的擰得出水來。近岸岩礁上的海藻、牡蠣、藤壺從酷寒中悠悠醒轉,丁香魚成群地在近海的岩礁之間迴游覓食;鷗鳥也三三兩兩在海面盤旋徘徊,時而低身俯衝,濺起一道白白的浪花。此時,村子裡都在忙著這一季「圍繒」(福州話唸成「偎津」)的大小瑣事。首要之務,就是將存放在魚寮裡的繒網拖出修補、染色。昔時魚網以黃麻、苧麻編織,泡過海水極易腐朽,每年圍繒前繒網都要用「薯榔」重新染過。「薯榔」約莫柚子大小,生得黑皮紅肉,模樣有點像芋頭,劈成細條後,放入石臼中搗擊成泥,移到木桶裡注入滾水,再將繒網浸入染汁中,攪拌揉搓。薯榔的汁液富含膠質,染過的繒網呈暗赭色,浸透膠質的纖維泛出黑沈沈的亮光,堅韌牢固。剩下的染汁丟棄可惜,順便把麵粉袋縫製的內褲置入浸泡,晾乾後成為深邃的棕色,布料也變得硬挺,可以當外褲,穿了去上學。
「清明穀雨,凍死老鼠(音ㄑㄩ)」,春寒料峭,家鄉的三月天還需穿上厚厚的冬衣。天未破曉,濱海石屋猶籠罩在大片的霧氣中,海岸傳來急切的奔走聲,幾個著短褲、穿桐油雨衣的壯漢,用兩根碗口粗的圓木,穿過繫在舢舨上的繩眼,彎腰合力扛起,疾步往海裡移動。一船六人,整日都在近海的礁岩間穿梭擺盪,撈捕丁香魚。濃霧中看不清船影,隱隱傳來搖櫓、撒網與收網的吆喝與喘息聲,每一個聲音都在撩撥家人企盼的心弦。
捕回來的丁香魚盛在細竹篾編成的簍子裡,圓潤透明,分不清每尾魚身的界線,有如盛載著一簍濃稠的蛋清,蛋清上有無數細細的黑點,那是丁香魚的眼睛。丁香魚嬌嫩如水,經不得太陽炙曬。魚寮內大鐵鼎的水已燒得滾燙,鹹度適中,輕輕舀入一瓢丁香魚,汆一下,魚身立刻轉成雪白,尾尾分明,好似蛋清熟成後如絮的蛋花。用竹篾製成的大杓子撈起後,盛在淺淺的竹籃子裡,一層層的架起陰乾。隔天端出,攤在太陽下風乾曝曬,整個村子都瀰漫著丁香魚鹹鹹的、帶一點海水腥味的香氣。煮丁香魚的湯水是不換的,只在原有的湯汁中不斷地加鹽添水,調整鹹度。一個魚季下來,湯汁都熬成了暗紅色的魚露,又鹹又香,各家都分得一些,用做沾料,或者調味;買回來的油條蘸一些魚露,忽嚕忽嚕地可以吞下一大碗公的地瓜稀飯。
那時我們上學,都要路經曬丁香魚的空地,一大片的丁香魚在陽光下泛著隱隱的青光。趁大人不備,隨手帶上一把已經曬成半乾的丁香魚,口袋鼓鼓的到學校,與友伴分食;講究一點的,還買了芝麻鹹餅,剖開後塞入一把原汁原味的丁香魚,細嚼慢嚥。彼時,我們的友情中都摻雜著丁香魚的滋味。風乾後的丁香魚會逐漸轉成微微的棕黃色,晶瑩剔透,像一粒一粒的羊脂玉,柔韌有勁;收進布袋紮牢,藏在廚房邊的碗櫥裡,過夏後,仍然滲出淡淡的魚香,就像記憶中坐在教室前排老師喜歡的女生,總是那般素靜、圓潤與甘甜。
自從國道四號開通以後,我家距離台中港的魚市場近了許多。以前為了買魚,或者更確切地說,為了嗅聞海風的腥味,要繞過清泉崗,經大雅、沙鹿、清水,才能到台中港的魚市集,車程來回幾近三個小時。現在假日外出,逛魚市變成選項之一,有時興致來了,沿著寬闊的臨港大道往海邊溜達,日落前拎回幾斤魚蝦、螃蟹,當然一定會有吻仔魚,不,是丁香魚。一番蒸、煮、燜、炸,通過嗅覺與味覺的回應,喚醒了記憶深處的兒時光景,身心就得到安頓了。
丁香魚,是一個巨大的、溫暖的符號,是一個從濃霧中散發親情與暖意的詞彙。聞著丁香魚,夢便伴著丁香魚的清香一路蔓延到故鄉的海邊、濃霧、石屋,還有欸乃的櫓聲。
轉載自馬祖資訊網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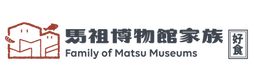




留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