馬祖辭典之二十三:肉絲麵
- matsu food

- 2019年7月29日
- 讀畢需時 7 分鐘
已更新:2020年3月9日
作者: 劉宏文
(一)
我第一次上館子,也是第一次吃肉絲麵,是在國小五年級。在那個物質匱乏、普遍貧困的年代,三餐已是左支右絀,自顧不暇,當然不可能父母帶著全家歡樂上菜館,我那生平首次的館店體驗,是馬祖防衛部的司令官買單的。
那天,島上有大官來巡,司令官親往碼頭迎接,層級可能是總司令或總長之類吧!我們馬祖國小的樂隊因地緣關係,也受邀列隊迎賓。隊員穿上大紅繡金線的樂隊上衣,兩列排扣金光閃閃,下身著白色滾藍條紋長褲,圓筒帽高高聳起,帽穗在風裡飄揚;大鼓、小鼓、鐃鈸、鈴鼓、直笛,排在隊伍前面,甚為威風顯眼。
從下午三點開始,迎賓的隊伍就在馬港的廣場等待,有穿草綠軍服的婦女隊,皮帶緊束蠻腰,有若紮著辮子的葫蘆;有穿著中山裝頭髮油亮後梳的公務員;有肩上搭掛星星、梅花、條槓的陸、海、空三軍;有赤膊穿紅短褲的蛙人,胸膛挺得老高就杵在樂隊旁邊。迎賓的隊伍排成兩路,蜿蜒夾道,逶迤成兩條長龍據滿海灘。
到了五、六點,太陽已經下山,也過了晚餐時間,不知為何,等待中的大官始終未出現。暮色籠罩,沙灘上的隊伍逐漸擾動渙散,有人坐下,有人走動,婦女隊員蹲成一圈聊天,小朋友更是蠢蠢欲動,坐立難安,只有蛙兵猶是直挺挺,紋風不動,黝黑的皮膚閃著隱隱的亮光。
等待的時光最是難挨。這時不知從哪裡來得靈感,老師要我們表演學校體育課剛教的翻筋斗,娛己娛人。打大鼓的阿德塊頭大,曲膝仰躺,雙手高舉,其餘小朋友輪番快跑至阿德前,雙手伸出按住兩膝蓋,藉著助跑之速,全身騰起,阿德順勢往上托,一個鷂子翻身,輕巧落在沙灘上,眾人拍手喝采;迎賓的隊伍逐漸聚攏,小朋友更是起勁,一個一個大展身手,在夜幕初降的沙灘上喧騰成五彩繽紛的飛輪。
迎賓結束,眾人散去,老師發給我們每人一張蓋了印章的紅色票券,說:「你們表現很好,
尤其翻筋斗,司令官笑咪咪,犒賞你們上館店。」事隔多年,我早已忘記那位大官的來頭與
長相,卻清楚記得十多位小朋友,怯生生、喜孜孜,有點受寵若驚,也有點不敢相信,夢一樣地坐在馬港舊街的館店裡。老闆在灶頭忙著,蒸氣氤氳,伴著煤灰的嗆味瀰漫周遭,門外圍著一圈聞風而來的小朋友,探頭探腦,眼露欣羨。老闆娘捧著木頭托盤,一次四碗,熱騰騰端出,麵上錯落有致排列五、六條嬰兒小指般的肉絲,點綴蔥花蒜苗。啊,肉絲麵!

(二)
吾鄉昔時稱餐館為「館店」或「菜館」,多位於街市繁華、人潮興旺的村落,南竿山隴、鐵板與馬港,北竿自然是塘岐,白犬有青番和大坪,東引則是「老鴨角」樂華村。館店內外擺設一眼見底,水泥灶頭連著食堂,圓桌方桌板凳條椅,灶台上一落鐵鼎,一座鋁鍋,鍋鼎長年滾著一盆水,油漬層積的檯面似有一層光澤。灶頭前掛著一串一串的排骨、豬肝、豬心、豬腸,血色慘澹不時滴落,巨大厚實的原木砧板箍一圈豬皮,平放矮櫃,其上擱著一大一小兩把菜刀,透出森森寒氣。店後門堆著煤炭,汙水沿屋角流過,貓狗嗅聞梭巡,許是燒煤炭之故,地面與牆壁都有一些烏黑。
幼時走過位於馬港舊街尾的館店,傳出厚厚沉沉的油香,食客多是軍人、公務員或晨起趕著搭船的旅客。館店沒有菜單,至多牆壁貼上幾片紅紙黑字,龍飛鳳舞,寫著各式菜餚。諸如:炒腰花、炒三鮮、炒肉絲、糖醋排骨、糖醋魚、紅糟鰻;湯類有太平燕、灴蹄膀、大小魚丸,還有鰻魚皮或帶魚勾芡發湯淋醋灑蔥花。
除了酒菜,館店也賣麵,按等級分陽春麵、肉絲麵、排骨麵,最高等級是豬肝麵。你若點一碗肉絲麵,老闆會在灶頭懸掛的五花肉選一角瘦肉割下,切絲,入鍋入料快炒,撈起備用,加水至餘汁煮沸,再散入麵條滾兩次,盛碗後補上肉絲。由於現切,煮出來的麵自有一股鮮肉的清香,不似現下麵店的肉絲都是絞肉機大量軋製,肉的紋理纖維糊成一團,再加上冷藏冷凍,難怪吾輩同學中,許多人變心改吃牛肉麵。
排骨與豬肝麵,當年在吾鄉屬於高檔奢侈品,除了食補或願賭服輸,一般人難得吃上一碗,我也僅止於聽聞,至今猶未嚐過。蓋島上東西兩守備區,每天大約只宰殺一、兩頭豬,就那麼兩副豬肝、豬心、排骨,早為館店商家預定。排骨可糖醋,豬肝炒三鮮,將之作為煮麵的配料,其豪邁與奢華可想而知。等到來台念書,方知豬肝其實不貴,但有抗生素的疑懼,也不敢放膽亂吃;至於排骨麵,吾家附近「豐原排骨麵」赫赫有名,我食過一次,一大塊滷排骨覆在麵上,就像火車賣得排骨便當,不是吾鄉所見一條一條的排骨切小塊;如此,吃排骨飯便是了,何必吃麵。
吾鄉漁農之家甚少進館店。那時家裡種菜,父母凌晨即起,挑菜到山隴、鐵板市集,盤給賣菜的小販,回到家已是八、九點,這才起灶拉風爐升火煮早飯。從未聽聞他們到館店、扁肉店、豆漿店叫碗扁肉、吃碗麵或飲一杯豆漿果腹。掙錢辛苦,在餐館吃食除了花錢,不貪嘴才是信守的美德。有一次父親來台,經過市場,大白天許多人在小攤吃喝,他見了若有所思,眉頭皺起,隨口冒出一句:「台灣人嘴這野(貪食)!」在吾鄉不是正頓時分,除非上工幹活,或師傅砌厝、受僱打樁,一般人是不隨意進食的。
那個年頭,白米珍貴,番薯是主食,偶而也吃麵。救濟分得的麵粉慎重其事地拿到製麵的店家,加入碱水絞成「切麵(音:欠棉)」可久存。「切麵」色黃,一般煮成甜的不須配料,上山下海幹活可當點心。煮肉絲麵則用「棋子麵」,白麵,小孩生病感冒,煮一碗熱呼呼的肉絲麵,吃完發一身汗,病就好了一大半。
吾鄉人最常吃的是「索麵」,稱「落索麵」。索麵味鹹,易煮易熟,水滾後汆燙一下即刻撈起,否則成了麵糊。索麵潑老酒、加煎蛋與紅糟雞肉是正宗,但現在市面賣的「老酒麵線」配的都是豬肉絲,就好像蠣餅餡不是蚵仔、牡蠣,而是一塊瘦豬肉。有一回在桃園八德見一招牌寫「福州麵」,停車探詢,原來是嫁來台灣的福州女子,30多歲,她煮的索麵即是以雞肉佐配,果然兒時風味,吃得我滿心感激,下一回再去,鐵門拉下已歇業,茫茫人海,不知散入何方?
(三)
在馬中念書六年都住宿,父母體念初轉大人,除了不再打罵,說話口氣也變得溫柔和煦,每星期還會給個5元10元的零用錢。那時青春年少,剛從荒僻小村來到竹篙坪,同學來自四鄉五島,對世界充滿好奇且躍躍欲試。那時最常探索的是山隴的掬水軒冰果店,還有學校後面陸軍醫院附設的福利社飲食部。星期日下午住校生都回來了,一夥人結伴,一盤四果冰,或者一碗陽春麵,這個星期的零用錢基本用罄,口袋空空,苦苦挨到下個禮拜的到來。
軍醫院的飲食部設在病房後面的一棟鐵皮屋裡,掌廚的是一位老士官,叼著菸,經常穿一件草綠色的汗衫,手臂上粗陋的「反共抗俄」刺青晃來晃去。福利社只賣陽春麵、肉絲麵和水餃。廚房內的汽化爐嘶嘶地吼著,必須不時打氣火力才能保持旺盛。鐵鍋旁擺著盛豬油的鐵罐,蔥花蒜抹,還有一大盒「鮮大王」味素。老士官滿頭大汗,左手持鍋鏟,右手拿瓢勺,汗水滴落火燙的鼎邊,滋的一聲,有肉焦味傳來。麵端出來,油花花一片,老士官端碗的大拇指有一半浸在湯裡。
那時拜「救總」與「嘉新水泥」之賜,每個學期提供獎助學金。特別是救總頒發的清寒補助金,每個月200元,全班大約有三成同學受惠。我有時領到,有時槓龜,沒個準,大概家裡有時清寒有時不清寒吧!有了錢就心神蕩漾,便會往更遠的食店探索,有時去中隴邊坡上的福利社,有時去顯然高檔一些位於警察局後面的小店;不免多花幾元點肉絲麵或水餃,但是回家得面對父母一頓口舌排頭。我一位同學的老媽就對他說:「人家依華200元一毛不少,他拉的屎都不要給你聞!」多年以後,哥們交心,他才倖倖說,這句話比挨揍還疼,讓他心理創傷了許多年。
在台北念書那幾年,同學多窩居新生南路一帶,日常吃自助餐,半工半讀,打拼未來,生活簡單而平實,頗負盛名的龍泉街牛肉麵就在附近。不過最常光顧的倒是溫州街角一間破爛帆布搭蓋的違建,老闆是一位退伍老兵,他賣陽春麵跟榨菜肉絲麵,也賣鴨脖子滷味;老士官、老同學、老味道,一切是那麼熟悉,彷彿身在軍醫院的飲食部。
有一回在貴州旅遊,行到一侗族山寨,飢腸轆轆,見一間極為簡陋的食店,非常像當年馬港舊街尾的菜館,一列十多道魚肉蔬菜已經洗淨切妥,置於碗盤排在灶邊,荒村野店也沒得選擇,點了幾樣,師傅開口:「是你炒,還是我炒?」我一時愣住,原來偏鄉僻地與吾鄉海島都一樣,從小土裡生、地上爬,跟著母親在灶頭燒火打雜,耳濡目染,誰不能拿起鍋鏟,叮噹五四,三下兩下湊和一道料理?
這幾年經歷了許多人事物件,也品嘗過眾多風味佳餚,青春就在百感五味的生活食色中耗散消逝,這時候特別懷念幼時菜館裡瀰漫氤氳的蒸氣,翻筋斗時瞥見殘留天邊的晚雲,以及那碗托盤端來肉絲麵的清香。而我知道,當腸胃不斷搜尋過往記憶,舌尖不斷回歸兒時場景,我卻於此際開始衰老。
(照片翻攝自馬祖日報編印《典藏馬祖》,特此致謝。)




轉載自馬祖資訊網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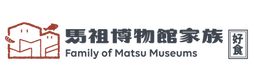




留言